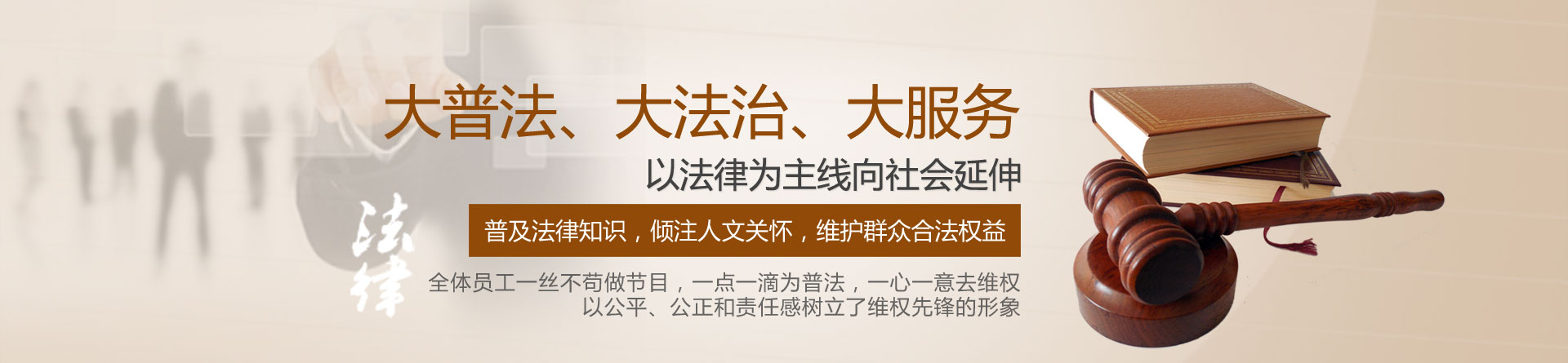【我的讼No.1204】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当事人在粤北某市经营一家五金加工厂,加工废水经过简单处理之后排入附近河道中。环保部门上门执法,发现所排废水中锌的含量超标36倍多,遂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要求刑事处理。等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后,检察机关觉得这个案子比较典型,同时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为该市**例公益诉讼案件。
我2006年开始便师从有“中国公益诉讼研究**人”称谓的颜运秋教授研究公益诉讼,在他门下读了硕士和博士,和老师一块做过不少课题,其中便有教育部唯一一个环境公益诉讼的重大攻关项目。我们也发表过一些公益诉讼的论文,对这一块的理论和实践还是比较熟的。检察院可能没想到,他们试水**个案子,便遇到了我这样的对手。
因为我的当事人被羁押,我尝试申请取保,到了检察院又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均没有成功。检察院要把这个案子做成**个公益诉讼案件,想争取不起诉是不可能了,我只好改变策略,催促和配合检察机关加快进度,早点起诉到法院,希望当事人能够快点出来。
检察院派了三名检察官出庭,一名检察官支持公诉,另外两名检察官对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发表意见。刑事部分指控我的当事人构成污染环境罪,民事部分要求他停止污染行为,赔偿环境污染修复费用9000多元,鉴定费16万元。
在刑案的质证阶段,因为检察院未提供取水样的视频,我不确认环保局监测报告的合法性和关联性,称无法确认取样来自当事人工厂的污水。锌是二类污染物,取水点应在排污口,而环保局是在水坑取水的,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若水深低于一米,应在二分之一处取水,而环保局是将沉渣一并取样,这也是不对的。此外,对含锌污水取样时应用酸荡洗试管,还要加酸酸化至1%,环保局并没有这样做。公诉人大约没料到我查了这么资料,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在民事公益诉讼部分的答辩时,我称起诉不合法,因为未督促环保局先进行行政处理,不符公益诉讼的谦抑性原则。此外,公诉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存在争议,因为公诉人的身份若是原告,则破坏民事诉讼的结构,违反民诉的基本原则。如果法院认为起诉合法,诉求也应驳回,因为工厂早已关停,停止污染的诉求已无必要;16万的鉴定费用是不必要的,花16万鉴定费,得出环境修复需要9000元的结论,实为故意加重当事人的负担。此外,赔偿款应该由哪个机构收取目前尚无法律规定,实际上无法操作。该起诉人可能对这一块研究较少,惟有念无关法条以应对。
法官问及量刑建议时,公诉人当庭建议缓刑,我松了一口气,这已经超出我们的预期。
休庭后,我坐在座位上等签笔录,两位民行科的检察官过来跟我探讨公益诉讼的谦抑性以及检察院的诉讼地位问题,聊了几分钟。女法官本来已经上楼了,又折回来问我:公益诉讼可以调解吗?我说我们这个案子民事部分应该可以调解。她转向检察官:那你们*好是调解吧。检察官同意了,说回去请示一下领导。
遗憾的是,调解一事没有下文,我们很快收到了判决书。当事人获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很快就从看守所出来。
我随导师研究公益诉讼十多年,刚开始做的时候,这个领域冷冷清清,到后来则炙手可热,投身其中的学者非常多,相关书籍和论文可谓汗牛充栋。当然,研究同质化非常严重,我们往往一看标题,就大体能猜到论文的内容会是什么。对于像我们这样的边缘研究人员来说,*开心的事情莫过于,我们当年所鼓吹的,渐渐的都变成了现实。到2012年,民事诉讼法确立公益诉讼制度,之后,环境保护法修订,增加环境公益诉讼条款。再到后来,渐渐有了一些公益诉讼案件,此后,又有了2018年前后公益诉讼案件的井喷,我们纸上写的,终于有了那么多鲜活的案例进入法庭,我自己还代理了一些这样的案子,真是不胜欣慰和感慨。
作者:周晓明,经济法博士,法学博士后,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要执业领域为公司与股权、争议解决、计算机及数据、刑事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