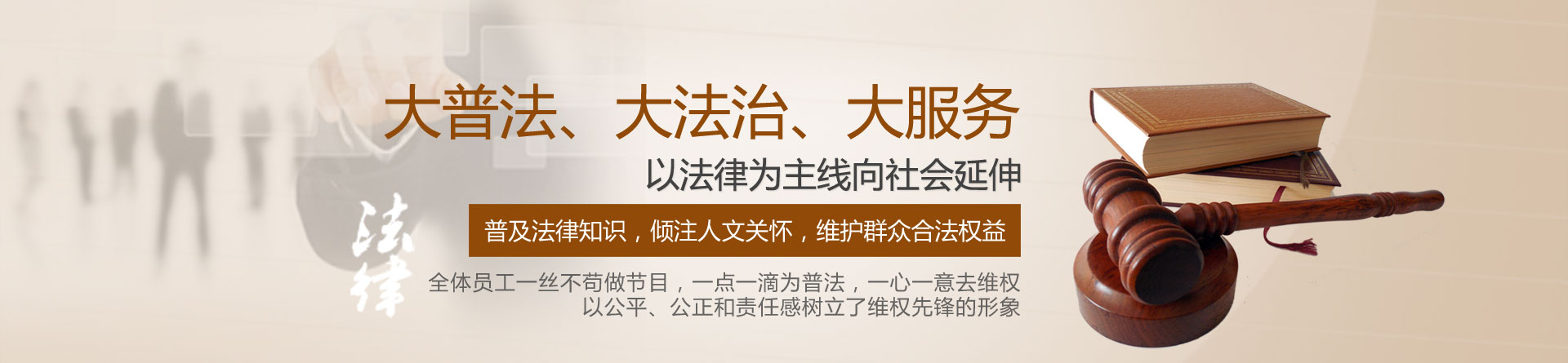【我的讼No.1132】顾问单位工伤案
顾问单位一位员工在操作机器时,被机器碾压到手,左手手腕及左前臂被压伤,劳动能力鉴定被评为六级伤残。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工伤六级,用人单位是不能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但这位员工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医疗补助金差额以及就业补助金。因为赔偿数额巨大,总数会超过30万元,用人单位希望劳动者作出一些让步,但劳动者不同意,用人单位干脆就拒绝支付,让劳动者去申请仲裁。
这个案子我完全没有印象了,应该是由助理代理的。我刚才查到了这个案子的上诉状,由此判断,这个案子打到了二审阶段。一般来说,一个案子经过仲裁、一审和二审程序,整个流程历时基本上会在一年时间以上,劳动者拿到工伤赔偿款的过程就会非常艰辛。他本身就伤得很重,在维权的过程中,想必也有许多心酸眼泪。
这种案子没有什么难度,也收不到多少律师费,但是它是顾问单位的事,我们没法推脱。我们当然不希望与这样的劳动者对簿公堂,更不希望通过繁复的诉讼程序来为他的维权增加难度,但职责所在,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民国法官吴经熊在判决犯人死刑的时候,都要向死者的灵魂祈求,要求它原谅他这么做,因为这是他的角色决定的,并非他的意愿。在代理这类案件时,我就常常会想起这个故事。
好在,工伤赔偿案件本身没有难度,虽然劳动者是One shotter,一辈子可能就打这一个官司,而用人单位是Repeat player,有丰富的诉讼经验,还有专业律师加持,但用人单位一般也难以在这种案子中讨到好处。在深圳地区,还有律师费用转嫁制度,劳动者请律师的费用也可能由用人单位承担,用人单位想为难劳动者的成本就会更高。有时候我也觉得,用人单位抵抗劳动者维权的努力也并不全是消极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会从反面推动法律的进步,深圳劳维案中的律师费转嫁制度就是这种抵抗的产物。
作者:周晓明,经济法博士,法学博士后,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要执业领域为公司与股权、争议解决、计算机及数据、刑事辩护。